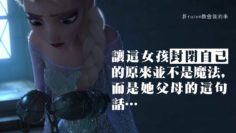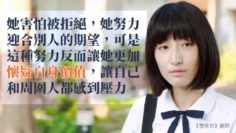#212 小Pooh
「我是小Pooh,在19歲那年曾經投稿到POPA,分享自己作為孩子的心聲,今年我28歲,正準備和另一半組織家庭。因為今次訪問,我又再一次回看了自己的成長。
現實迫使我長成一個懂事的孩子
我的家庭其實有點不太尋常。我的媽媽本身受情緒病困擾多年,爸爸也很火爆暴躁,加上弟弟是自閉症譜系,從小就不太能夠處理自己的情緒,於是我彷彿就是家中唯一『正常』的那位。
弟弟時常會惹怒父親,家中屢屢發生『暴力』事件,總是瀰漫著大事即將發生的緊張感,媽媽則因為承受不了家中的壓力,長年不在家,多半是去了賭錢。我從小習慣負責當處理及善後的人,小至收拾家中摔破的東西,大至幫助解決媽媽的負債。
記得小時候,弟弟每當情緒爆發我都會打給媽媽,但久而久之,我發現事情既已發生,媽媽不一定會即時回來,即使她回來,通常弟弟也已經平伏下來,於是漸漸我就不再告知她:『弟弟又鬧事了』。像有一次,弟弟發脾氣摔破了家中的碗碟,同樣是小學生的我,就默默把玻璃碎掃清,受傷的地方包紮好。我心裡也想著『別要再讓媽媽添煩』就好,不會想去圖個讚賞,更多的時候也希望媽媽不會被一直提醒『我的兒子有問題』。
在別人眼中,我或許是如此懂事的孩子。也因為懂事加上成績不錯,其他人總覺得『我搞得掂』,於是一路成長,身邊的大人都很少問我的需要、我的感受,我就像隱形人一樣。在弟弟進到特殊學校之前,我和他同校。在學校裡,我是XX的姐姐,也是他的半位『家長』。明明只比他大幾年,但只要他在學校生出事端,老師都是第一時間找上我,彷彿他的行為問題就是我的責任。
對於原生家庭的傷痛,我沒有恨
寫到這裡,或許會有人替我不值,覺得我的父母沒有做好他們的角色,但我分享自己故事的其中一個原因,正正就是想說,我的父母可能不是社會定義的好母親好父親,但我從來沒有恨他們。也許在青少年時期,我也有反叛,但現在回望,我仍然愛我的父母家人,也感恩這成長經歷構成了現在這個我。
那現在的我是怎樣的呢~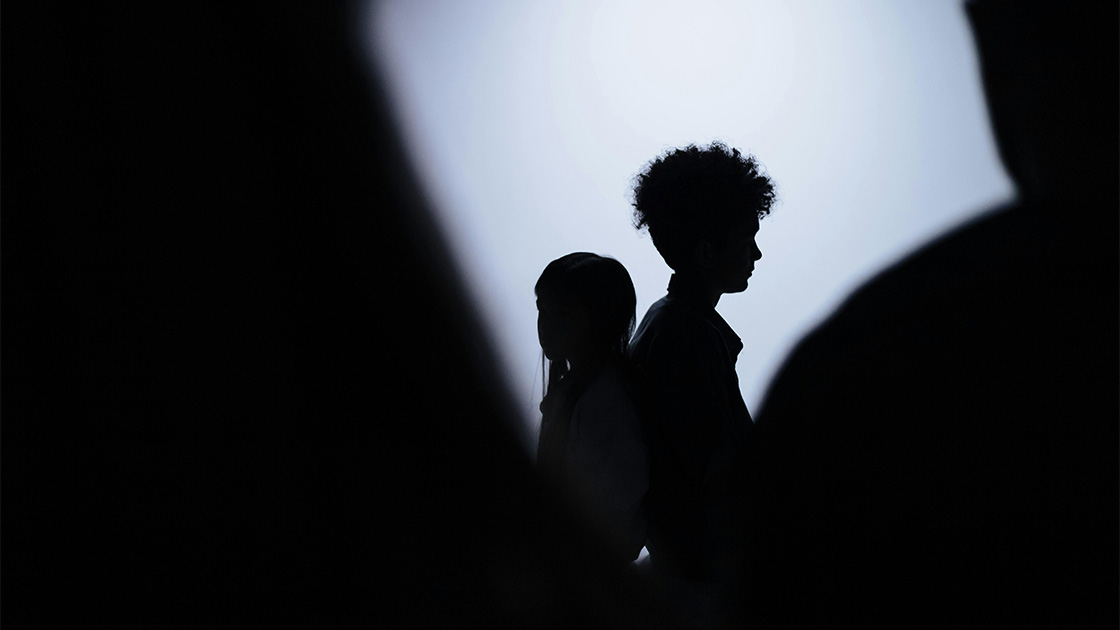
我不會說我全無成長傷痛或創傷,畢竟當母親跟你說『你別期待我會呵護你,我能力上做不到』,你不可能沒感覺,只是,我同時理解她作為長期情緒病患,她真的沒能力以我心中期待的方式來呵護我。曾經有一段日子,我見社工、見心理學家、見精神科醫生,把心的碎片慢慢重新整合。當我知道並接受母親已盡其所能,用她的方法去愛我,這個『知道』幫助了我相當多。正如我之前那篇文所寫,19歲那年,我因為她重拾了書本,為自己的人生而努力。
我感恩自己作了這樣的決定。
還有就是,小時候被當成是半個家長,我的確被迫長大,但正因如此,我從小就接觸教養及兒童發展心理的知識,影響到我在大學時選修了心理學。畢業數年有幸一直從事教育工作,陪伴下一代孩子成長。我因為自己的成長經歷,找到了人生意義。

我們無法選擇原生家庭,卻能選擇回應它的方式
當然,有時以為癒合了的傷痛,偶爾還是會被觸發。
像一次我在家中焗蛋糕,一不小心把食物摔一地。那刻像極了小時候弟弟摔破碗碟的聲音,我整個人愣住。我著男朋友不用幫手,自己默默地把盤子收拾,心中不斷抗衡那些自我批判的負面聲音,而另一半的一句『有無事?不要緊,小問題!』已經給我很多溫暖。不久後,門鈴響起,原來他知道我會很失落,於是馬上Order了同款蛋糕的外賣。那一刻在我腦海想起了心理學教授提及過,即使一個人因原生家庭而發展焦慮矛盾的依附關係,一位安全型依附的另一半卻能幫助我去學會冷靜,學會信任,學會看見自己的好。
過去我也曾因為自己從來不受重視,而錯信了別人口中說的愛,但這些跌碰並不是沒意義的。正如原生家庭給予我們的挑戰一樣。
原生家庭的確影響我們很多,但最終我們如何理解和回應這些經驗,將能決定我們的下半生。

現在我的家的緊張感已鬆弛多了。弟弟從學校畢業後,回到家中,情緒還是偶爾爆發,但相對已經能和父母平靜相處,亦努力工作獲得不少同事的支持及嘉許。我早些時候決定和男友同居,搬離了成長的那個家,本來以為母親會反對,她卻沒半點阻撓。有些人或者會覺得媽媽很冷漠,但我卻樂於放下原生家庭給我的枷鎖,有種『我自由了』的感覺。間中當然也會自省我是否太自私,他們會否仍需要我更多的支援?但原來只要我選擇放下,我就能夠好好照顧自己,規劃自己的人生。我和另一半也正計劃組織自己的家庭,把我們滿滿的愛傳承下去。
我的前半生成長路,的確滿是波折,不過我深信現在已經On the right track,我期待著接下來由自己決定的人生,即使有再多高低,我都能平靜走過。」
受訪者:小Pooh
圖片來源:Pexels
🔹POPA家長支援服務🔹
我們的團隊來自不同界別,分享共同理念:關顧孩子成長,陪伴家長同行,期望以自身專業,為家長及孩子提供適切支援,包括教養諮詢|家庭治療|兒童為本遊戲治療|個人輔導|伴侶/婚姻輔導等,如你也希望有人同行,聆聽你現在的困難,可按這裡了解詳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