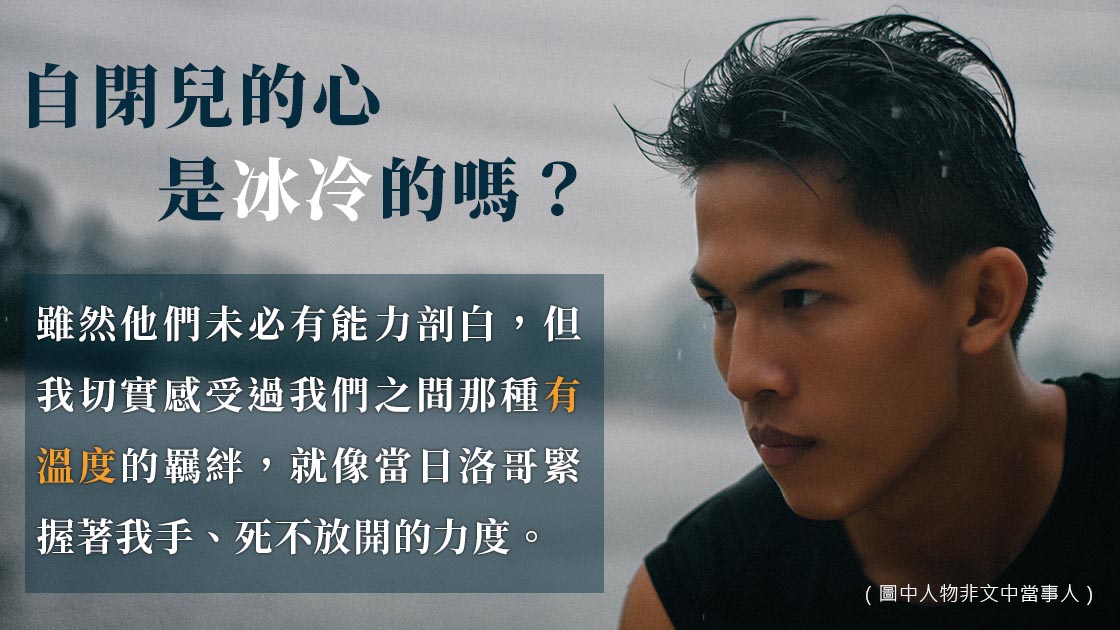有一天,我在言語治療室處理文件。突然有一個敏捷的身影闖入了我的治療室,他一個箭步衝過來,大力緊握我的雙手,眼睛也緊緊盯著我看,彷彿有千言萬語想立即跟我講。我定睛一看,哦,原來又是我的學生洛哥。
在特殊學校工作了多年,我早已練就金剛不壞之身,對「有刺客」之事都能處之泰然。但我再仔細看看,為什麼洛哥的頭髮不停滴著水珠?為什麼治療室的地下滿是黑黑的鞋印?定神想到:今日不是放暑假嗎?為什麼他會此時此刻出現在學校?!!!
此時,治療室外正好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:「姑娘!宿舍打嚟話洛哥又唔見咗!」我連忙捉實洛哥的手不讓他離開(事實上我也如獵物般被他緊緊地捉著),一邊開門對氣急敗壞的老師說:「係呀佢又密室逃脫喇,而家我喺佢手上。」
我就是他的刻板興趣
之前的文章提及過,洛哥是一位自閉症、深度聽障和智障的高中學生。如果說大部份自閉兒都有自己高度刻板、固定的奇特興趣,不知幸或不幸,這人的興趣正正在於姑娘本人和言語治療室。
無論在學校的哪一個角落,他的眼睛總是斜視著言語治療室的方位。他更好像一個永遠準備起步的奧運障礙賽選手,一有機會他就會突破重重障礙,盡情地奔跑到言語治療室,找我。
我的朋友們聽到我的經歷,都笑說這是非常浪漫的偶像劇橋段啊,不顧一切披荊斬棘地跑來找你。但發生洛哥身上,就一點也不浪漫了——我們每次都害怕他走失,害怕他發生意外。今次他更變本加厲,在距離學校幾個地鐵站的暫託宿舍、冒著傾盆大雨、身無分文地不知道用什麼方式跑來學校,實在嚇得我們和老師們膽戰心驚。
第一次的心靈接通
那麼,到底我什麼時候開始成為洛哥的刻板興趣呢?我自己反思,可能自從他從我身上嚐到溝通的甜頭?
身為一位比較聰明、但聽障非常嚴重的學生,他大概總在課堂感到孤獨又寂寞吧。我想像,洛哥在課堂上經常聽不清楚老師的講課,無錯他會用溝通簿表達想法,但表達的內容總是在課室中不能實現,例如他想畫畫、想去言語治療室、想玩玩具……而授課中的老師又總不能永遠全神貫注在他身上。
言語治療課就不同了,姑娘總是一對一地與他上堂,把完整的專注力傾注給他。想玩玩具嗎?姑娘會引導他表達清楚想玩哪一款玩具。想畫畫嗎?姑娘會陪他玩「估估畫畫」的遊戲。
我永遠難以忘記,我第一次誤打誤撞與洛哥玩起「估估畫畫」的情景:當我在溝通簿上準確地指出他畫的物件,他向來漠然的眼神中竟然燃起幾分喜悅的火花,是我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的。
那一刻,我知道,他開始接納我,他放下了防衛和冷漠,接納我走近他的生命。只是沒有想到,這種心靈接通的經歷,從那次「估估畫畫」之後竟成為令他不停「走佬」的身體記憶。
我與他之間是一種超乎血緣的羈絆
雖然洛哥經常「走佬」行為令我很頭痛,我和老師們事後亦想了很多方案應對。但仔細想想,我還是很榮幸他曾經挑選我成為他的刻板興趣。我身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,能被一個自閉兒「睇得上眼」、「放在心上」,而他能在我身上找到溝通的慾望和滿足,本身不已是一件無限奇妙的好事嗎?
這些年我憑藉著洛哥對我的特殊信任,訓練他用溝通簿表達更多不同的意念,手把手教他打出簡單的手語。有時我又好像在教海倫凱勒般,逐個音節與他做聽覺和讀唇訓練,希望他可以善用剩餘的聽力。
一開始我只隱約覺得自己在海市蜃樓蓋一棟不知名的大樓,我根本不知道我輸入的他能接收幾多。不過日復日的建築過程,卻是實實在在又充滿愛的。我只知道每次我召喚他出來上治療課的時間,他冷淡的臉上總會偷偷掛著一絲得意的笑容。
「如果你馴養了我,那我的生命就會充滿了陽光,你的腳步聲會變得跟其他人的不一樣。其他人的腳步聲會讓我迅速躲到地底下,而你的腳步聲則會像音樂一樣,把我召喚出洞穴。」《小王子》中的狐狸這樣說。
如果再有人跟我說自閉兒的心全然冰冷,我會堅定地回答:雖然我看不見他們的心,他們也終究未必有能力向我剖白,但我切實感受過我和他們之間那種有溫度、超乎血緣的羈絆,就好像當日洛哥曾經緊握著我手、死不放開的力度。
那對我而言,是一個他武力上制服了我、但我心靈上馴服了他,一個微小但感動的重要時刻。
*文中人物為化名
圖片來源:Unsplash, Pexels